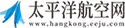在北影节的“修复经典”单元,我们得以看到小津安二郎1948年的作品《风中的母鸡》。重新品读这部作品时,或能咂摸出不一样的味道。
小津安二郎1948年的作品《风中的母鸡》讲述的是二战后复员归来的丈夫,无法接受妻子战时曾因为儿子生病没法筹得医药费而有一夜卖淫的经历。他痛苦不堪,甚至做出强暴妻子和将其推落楼梯的暴力举动,夫妻最终艰难地达成和解。
本片在《电影旬报》与黑泽明的《泥醉天使》、沟口健二的《夜晚的女人》及清水宏《蜂巢的孩子》同列当年十佳,评价不低,但却饱受一些影评人的抨击。小津也罕见地自嘲本片为“无益的失败之作”。老友野田高梧直言它对世相的反映流于表象,对其处理手法也难以苟同。
 【资料图】
【资料图】
叫好的声音虽少也有,如佐藤忠男就认为电影透过废墟布景等道具重现了当时荒芜的风俗行业,比任何作品都更深入地探讨了战败的问题,且描绘了日本人丧失的纯洁。又说,在战败后的日本电影中,没有哪一部比得上它怀着如此深切的悲痛之情,描绘了日本人对于失去的苦涩和悲叹。
随着对小津研究的深入,近年对《风中的母鸡》的评价也有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它是有缺陷的力作。其缺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影片的基本构思来自于小津喜爱的作家志贺直哉的小说《暗夜行路》。这使影片成为带有“志贺色彩”的小津作品。小津从不掩饰自己对“小说之神”志贺作品的喜爱,他在战时日记中写到曾在中国战场上读过《暗夜行路》:“前篇读了两遍,后篇开始读,为其内容的激烈所触动。这是多年未曾有过之事。深受感动。”
“内容的激烈”指的是后篇男主角发现妻子出轨后难以释怀的心理痛苦,高潮是他粗暴地将准备搭火车的妻子推下月台。“妻子犯错”和“丈夫将妻子推下月台”的情节,令小津大受震撼,并移用为《风中的母鸡》后半部分,同样令观众大受震撼。将妻子推落楼梯的场景是小津所有作品中最狂暴、最激烈的段落。影评人竹林出指出妻子倒地的姿态“呈现出垂死昆虫似的肢体动作,那姿态俨如饱受战火摧残的日本”,从而令日本观众产生强烈共鸣;导演吉田喜重更称本片为小津的“愤怒之作”。
不像很多日本导演,小津在战后很快就将战争的挫败感抛于身后,心情愉快地拍起反映战后民主的电影。但他不解决纠缠于日本人(包括他自己)心中的战争阴影,就没办法前进(直到遗作《秋刀鱼之味》,他才以“日本输了是好事”的台词完全将战争放下)。事实上,小津拍《风中的母鸡》的目的,不只是痛感日本丧失了纯洁,而是要为“茫然自失的日本人带来勇气,更进一步透过电影实践他在战场上获得的体认。”
所谓小津在“战场上的体认”,是指他经过战场的洗礼——在日记中写下“文学自当以文学具备的全部力量襄助国策”,又在参战归国后说不想再拍表现怀疑的电影,并产生了“肯定的精神”。论者指出,这意味着他确认了“集体意识的存在”,开始思考日本人(及其子孙)的责任感,并反映到了作品中。最明显的是,战前他的作品均以家庭和个人为主题,是完全的个人世界;而他战时的作品《父亲在世时》里,父亲依循着明治时代以来富国强兵、近代化的国策,将儿子送进大学,又在战时勉励儿子努力工作,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做好自己的事,以此效忠社会和国家。这种个人对集体意识的认同,是他战前的作品完全没有的主题,如在类似题材的战前作品《独生子》中,母亲只不过希望儿子能够出人头地,并无效忠国家的大志。
在《父亲在世时》里,个人的命运(学习和工作)与集团意志(国策)水乳交融。《风中的母鸡》也同时处理两个主题(表面主题为夫妻和解,深层主题则是战后疲惫不堪、流离失所的日本人如何与自己和解并重新出发),可它的思路却是挪用志贺的私小说《暗夜行路》的心理分析。私小说关注的是个人的小世界,小津欲以私小说的情节和主题来处理日本人战败后的集体心理这个复杂沉重的主题,就捉襟见肘了。
夫妻之间的和解属于个人问题,而日本人的重新出发是超越了个人的集体意识问题,两种意识没法捏合。小津对两个主题的描绘都失败了:在个人层面,他虽借鉴了志贺私小说的心理分析,但志贺用大篇幅文字描述的丈夫的痛苦心理,小津却没能以影像成功刻画,欠缺了他的主观角度,包括对战争及战败的严肃思考和反省(妻子之所以一夜卖淫,不正是由他所参与的战争引发的吗)。集体意识层面,他欲用妻子“犯错”的私小说情节来缓解日本人集体意识的失落并重新出发,这是不可能的,得像木下惠介那样拿出大魄力(《大曾根家的早晨》和《日本的悲剧》为反思战争杰作)才行。
小津想必也意识到了《风中的母鸡》中私小说的情节无法与集体意识捏合的缺陷,才在野田高梧的帮助下吸取了教训,终于凭借《晚春》的成功迎来导演生涯的第二春。他的做法是回归《父亲在世时》的处理手法,只不过将“父子关系”改为“父女关系”,将“把儿子培养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改成“让女儿结婚”。
《晚春》中父亲要求女儿(相亲)结婚,出于某种义务感,也是随当时的日本社会集体意识的大流。这就与《父亲在世时》一样,个人生活与集体意识扭结在一起,自然引发观众共鸣。有意思的是,片中的女儿属于小津战前作品表现的个人主义者。对她而言,结婚等于破坏了她原本和父亲共度的宁静和幸福的生活,而对于父亲结婚一事的强烈愤怒超出了她个人的框架,最终却又无奈地走向对集体意识的认同——出嫁。
竹林出说,《晚春》里的女儿所象征的是一个接受了精神(个人)死亡之后重生的故事。正因为接受了牺牲(个人的死亡),结婚——也就是重生——便具有重大意义,值得人们祝福。实际上,小津战后的嫁女题材,充满了这种个人和集体意识的矛盾,表现为更西化的年轻一代和更抱持传统价值、认同集体意识的保守老一代之间的争执,小津只不过反向操作,将年轻一代急于挣脱上一代的心情,逆向表现为老一代对新一代的理解和放手,新一代反而表现出对老一代的眷恋和不舍(其实是牺牲)。他错综的创作心理是值得玩味的。
这正是小津没能透过《风中的母鸡》让因战争而伤痕累累的日本人与自身达成的和解(重新出发)的要素。《晚春》承袭了《父亲在世时》的方法论,同时达成了《风中的母鸡》所要追求的目标。